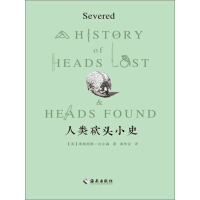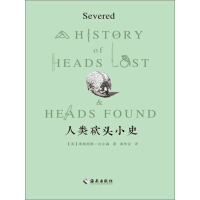内容简介
人类的头是一件了不起的作品。在五种官能中,单单是头部就掌控了其中的四种,它严密地包裹住大脑,并且拥有整个身体富有表现力的肌肉群。
头是人类极具区别性的特征,将我们的内心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尽管头拥有如此超群的能力,但也经历过黑暗时期,在人类历史上,主要表现为斩首或割取敌人首级。无论是一些西方的收藏家对干缩头颅的需求激发了大屠杀,还是二战中美军士兵把日本人的残肢送回亲人身边,无论是杜莎夫人将被斩首的罗伯斯庇尔的头做成塑像,还是达米恩?赫斯特在停尸房拍那些被砍下来的头颅,无论是盗墓骨相学家还是痴迷于头骨的科学家,人类学家弗朗西斯?拉尔森探究了我们这种对被砍掉的头颅的一种可怕的迷恋,并对此进行了严肃深入且有趣生动的探究。
《人类砍头小史》研究充分,文辞极为精妙,其发现影响深远。当然,不可避免地具有黑色幽默性质,每章中关于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披露描绘技巧娴熟,又异常扣人心弦。此外,本书还会经常挑战读者关于文明与野蛮、西方世界与“其他世界”、暴力与医学、宗教与礼教之间的二分式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