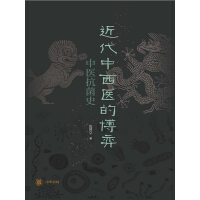
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百度网盘pdf下载
作者:
简介: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19-05-06
pdf下载价格:0.00¥
免费下载
书籍下载
内容介绍
编辑推荐
1.近代中医在“废医案”的洗礼下,团结起来自觉寻求中医的出路。在西医细菌学的冲击下,中医学人不放弃对传统气论的坚守,仍然以《伤寒论》等经典医书为圭臬,以中医的“毒”、“疠气”等概念对应“细菌”,对细菌说并非全然排拒,而是主动融汇贯通。在形势紧急之下,他们追求中医在学理上的被认可,对中医医籍和医案有所整理与吸收,对中医技术则少有发展。在他们的奋力自救下,中医得以幸存,而对中医技术的发展则是他们留给后世的待完成的使命。
2.近代知识分子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全面审视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有全盘吸收和保守主义两种态度。同样,他们对中医的态度也出现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其中医者以余云岫和恽铁樵为代表,其他知识分子以鲁迅和章太炎为代表。也有人既尊崇民族医疗传统,又吸收西医实验技术,如于右任以西医实验诊断病名,又以传统中药来治疗疾病,收到好的治疗效果。在民族自信深受打击的近代,知识分子对本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矛盾心理可见一斑。
3.现代中医如何走出百年来“废医案”的阴影,在中西医并存的医疗体制下有更大的作为,是近代中医留给现代中医的历史使命。近代中国国运衰微,传统文化包括中医式微,幸而文脉未断。而今民族自信高扬,如何继承中医的优秀传统并发展之,如何摆正中西医的位置,也是现代中医面临的时代课题。
2.近代知识分子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全面审视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有全盘吸收和保守主义两种态度。同样,他们对中医的态度也出现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其中医者以余云岫和恽铁樵为代表,其他知识分子以鲁迅和章太炎为代表。也有人既尊崇民族医疗传统,又吸收西医实验技术,如于右任以西医实验诊断病名,又以传统中药来治疗疾病,收到好的治疗效果。在民族自信深受打击的近代,知识分子对本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矛盾心理可见一斑。
3.现代中医如何走出百年来“废医案”的阴影,在中西医并存的医疗体制下有更大的作为,是近代中医留给现代中医的历史使命。近代中国国运衰微,传统文化包括中医式微,幸而文脉未断。而今民族自信高扬,如何继承中医的优秀传统并发展之,如何摆正中西医的位置,也是现代中医面临的时代课题。
内容简介
近代中医面临“废医”的生死存亡考验,一旦失败将万劫不复。基于传统气论与细菌学的近代中西医博弈,既是一场学理和技术的博弈,更是一场话语权和生存权的争夺。博弈的结果是西医胜出,中医在自救中得以幸存,为重生赢得一线生机。
近代中国国运衰微,中国传统文化也面临危机,中医同样如此。而今,抗生素的弊端日益明显,中医的技术价值也在发扬,如青蒿素的发现,这一切都说明这场关乎中西文化冲突的博弈至今没有停止。
本书立足于以中国医学视角书写中国现代史,聚焦近代中医学与细菌学的各种交锋、对话、排拒与汇通,力图重现中医在西医的科学实验及一步步占据国家卫生主权的过程中,如何运用自身的外感热病知识体系构建中医式的传染病学,并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中医理念和药物可以发挥效用的空间。重现这段历史,意在唤醒中医对自身体系的认识与自信、变革与创新,帮助大众了解中医文化的价值,走出百年来“废医案”的阴影,也为个人的实际治疗与日常养生,提供另一种思考的可能性。
近代中国国运衰微,中国传统文化也面临危机,中医同样如此。而今,抗生素的弊端日益明显,中医的技术价值也在发扬,如青蒿素的发现,这一切都说明这场关乎中西文化冲突的博弈至今没有停止。
本书立足于以中国医学视角书写中国现代史,聚焦近代中医学与细菌学的各种交锋、对话、排拒与汇通,力图重现中医在西医的科学实验及一步步占据国家卫生主权的过程中,如何运用自身的外感热病知识体系构建中医式的传染病学,并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中医理念和药物可以发挥效用的空间。重现这段历史,意在唤醒中医对自身体系的认识与自信、变革与创新,帮助大众了解中医文化的价值,走出百年来“废医案”的阴影,也为个人的实际治疗与日常养生,提供另一种思考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
皮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现任台湾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医疗史与人文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中医医史文献学会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医疗社会史、疾病史、身体史、中国近代战争与科技方面的研究。著有《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台湾日日新——当中药碰上西药》、《“气”与“细菌”的近代中国医疗史——外感热病的知识转型与日常生活》、《国族、国医与病人——近代中国的医疗和身体》,合编《卫生史新视野——华人社会的身体、疾病与历史论述》、《药品、疾病与社会》。
目录
版权信息
序 中医抗菌事,得失寸心知
自序 有“生命”的医疗史
绪论 中医史与细菌学何干?
第一节 “无中生有”的中医疾病史
第二节 浅谈医疗史研究
第三节 内外史的距离
第四节 从热病的近代转型谈起
第五节 新医史的尝试——“重层医史”
第一章 近代中西医在抗菌论述前的汇通
第一节 中西医初遇时的热病样貌
第二节 瘟疫何处生?
第三节 中西医的身体内外——感受与致病
第四节 中西治疗与预防文化的初遇
第五节 从似曾相识到貌合神离之前
第二章 抗菌书籍史——民国中医的外感热病文献
第一节 前 言
第二节 古典医书之再刊行
第三节 西方医学的影响与“中医传染病学”渐趋成型
第四节 日本医书的影响
第五节 古典医学在民国时复兴的几条线索
第六节 “再正典化”(renewed canonization) 的传统中医文献
第三章 中西医诠释疾病的历史——“伤寒” (Typhoid Fever) ——病的既存与再生
第一节 前 言
第二节 伤寒“西名汉译”之源流
第三节 “伤寒”的中国医学脉络
第四节 另一种声音——温病学的脉络
第五节 病名重释或在中西论争中消亡
第六节 中医的新伤寒论述
第七节 翻译、诠释与再生的中国医史
第四章 菌与气——民国中医对西方细菌论的吸收、排拒与汇通
第一节 前 言
第二节 西方细菌学的轨迹
第三节 中医吸收细菌说之发轫
第四节 章太炎“据古释菌”之例
第五节 中西医对细菌学论争的焦点之一——对气论的坚持
第六节 中西医对细菌学论争的焦点之二——观察、实验方法与治疗学
第七节 治疗细菌性传染病的思维
第八节 “亚学西还”的中医细菌学论述
第五章 新中医的实践与困境——恽铁樵谈《伤寒论》与细菌学
第一节 弃文从医的经过
第二节 恽铁樵之历史地位与本章问题意识
第三节 从古医籍中寻求灵感——读书与临症的再定义
第四节 攘外必先安内——“叶派”流毒与学术反思
第五节 恽铁樵对细菌学的认识与回应
第六节 对中西医病名定义之讨论
第七节 民初中医的困境
第六章 气与个人——中医热病学的身体、疾病与日常空间论述
第一节 前 言
第二节 微生物的现代性与“个人”卫生诞生之社会背景
第三节 细菌学之外:中医视角下的外感热病与“气”的位置
第四节 侧写反细菌视角:中西医汇通下的疾病观
第五节 中医的防病论述及日常生活的转型
第六节 热病的医疗空间、居处与日常生活
第七节 中国“个人式卫生”的反思
第七章 民国中医的防疫技术与抗菌思想
第二节 民国中医对防疫问题之检讨
第三节 实际案例:山西太原
第四节 防疫药品——消毒杀菌话语之转化
第五节 薰香:空气、消毒与清洁
第六节 探索失落的中医防疫技术
第八章 调养、饮食与禁忌——古典理论在病患世界的转型
第一节 前 言
第二节 古典食物禁忌学说和热病之关系
第三节 近代身体观转型之一例——气与抵抗力
第四节 饿不死的伤寒
第五节 西方的营养、中国的禁忌
第六节 热病后之“虚”与“复”
第七节 个人的卫生现代性诞生——气、血、精身体观的延续与转化
第八节 “现代卫生的异域”—— 中医式调养
结论 用中国医学书写中国现代史
第一节 检讨:贡献与局限
第二节 西风又东风——传统医学视角的文化史
第三节 “重层医史”视角下的医疗史与国史
序 中医抗菌事,得失寸心知
自序 有“生命”的医疗史
绪论 中医史与细菌学何干?
第一节 “无中生有”的中医疾病史
第二节 浅谈医疗史研究
第三节 内外史的距离
第四节 从热病的近代转型谈起
第五节 新医史的尝试——“重层医史”
第一章 近代中西医在抗菌论述前的汇通
第一节 中西医初遇时的热病样貌
第二节 瘟疫何处生?
第三节 中西医的身体内外——感受与致病
第四节 中西治疗与预防文化的初遇
第五节 从似曾相识到貌合神离之前
第二章 抗菌书籍史——民国中医的外感热病文献
第一节 前 言
第二节 古典医书之再刊行
第三节 西方医学的影响与“中医传染病学”渐趋成型
第四节 日本医书的影响
第五节 古典医学在民国时复兴的几条线索
第六节 “再正典化”(renewed canonization) 的传统中医文献
第三章 中西医诠释疾病的历史——“伤寒” (Typhoid Fever) ——病的既存与再生
第一节 前 言
第二节 伤寒“西名汉译”之源流
第三节 “伤寒”的中国医学脉络
第四节 另一种声音——温病学的脉络
第五节 病名重释或在中西论争中消亡
第六节 中医的新伤寒论述
第七节 翻译、诠释与再生的中国医史
第四章 菌与气——民国中医对西方细菌论的吸收、排拒与汇通
第一节 前 言
第二节 西方细菌学的轨迹
第三节 中医吸收细菌说之发轫
第四节 章太炎“据古释菌”之例
第五节 中西医对细菌学论争的焦点之一——对气论的坚持
第六节 中西医对细菌学论争的焦点之二——观察、实验方法与治疗学
第七节 治疗细菌性传染病的思维
第八节 “亚学西还”的中医细菌学论述
第五章 新中医的实践与困境——恽铁樵谈《伤寒论》与细菌学
第一节 弃文从医的经过
第二节 恽铁樵之历史地位与本章问题意识
第三节 从古医籍中寻求灵感——读书与临症的再定义
第四节 攘外必先安内——“叶派”流毒与学术反思
第五节 恽铁樵对细菌学的认识与回应
第六节 对中西医病名定义之讨论
第七节 民初中医的困境
第六章 气与个人——中医热病学的身体、疾病与日常空间论述
第一节 前 言
第二节 微生物的现代性与“个人”卫生诞生之社会背景
第三节 细菌学之外:中医视角下的外感热病与“气”的位置
第四节 侧写反细菌视角:中西医汇通下的疾病观
第五节 中医的防病论述及日常生活的转型
第六节 热病的医疗空间、居处与日常生活
第七节 中国“个人式卫生”的反思
第七章 民国中医的防疫技术与抗菌思想
第二节 民国中医对防疫问题之检讨
第三节 实际案例:山西太原
第四节 防疫药品——消毒杀菌话语之转化
第五节 薰香:空气、消毒与清洁
第六节 探索失落的中医防疫技术
第八章 调养、饮食与禁忌——古典理论在病患世界的转型
第一节 前 言
第二节 古典食物禁忌学说和热病之关系
第三节 近代身体观转型之一例——气与抵抗力
第四节 饿不死的伤寒
第五节 西方的营养、中国的禁忌
第六节 热病后之“虚”与“复”
第七节 个人的卫生现代性诞生——气、血、精身体观的延续与转化
第八节 “现代卫生的异域”—— 中医式调养
结论 用中国医学书写中国现代史
第一节 检讨:贡献与局限
第二节 西风又东风——传统医学视角的文化史
第三节 “重层医史”视角下的医疗史与国史
前言
序 中医抗菌事,得失寸心知
张仲景的《伤寒论》无疑是中国医学史上最为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这部向被视为众方之祖的医书,也多被看作是中国临床医学的开山之作。该著在宋以后,开始受到诸多医家的推崇而日渐正典化,到明清时期,伴随着张仲景医圣地位的确立,《伤寒论》也渐趋成为与儒学中的《四书》相类的医学经典。与此同时,明清特别是清代的医家,还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温病学说”。这一学说,在诸多的中国医学史论著中多被看作是明清医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以是观之,我们应该可以毫无疑义地认为,对“伤寒”、“温病”等疾病的认识和治疗,乃是中国传统医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这些疾病,按照今天的疾病分类,大体均可归之于外感性疾病,即由致病病原体导致的感染性疾病,也就是广义的传染病。按照当今医学的认识,这类病原体种类甚多,其中主要有细菌和病毒,不过在20世纪病毒被确认之前,学界和社会往往都以细菌名之。这也就是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对于由病菌引发的外感性疾病的诊治,不仅是中国医学关注的重点,也可谓是其特长。
然而吊诡的是,尽管近代以降,张仲景和《伤寒论》的地位不断地被确认和提升,一代代的中医学人也对“伤寒论”和“温病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做出了极其丰富的研究和建构。然而,放眼现实,却不得不承认,治疗由病菌引发的外感性疾病,早已不是中医的主战场,甚至在一般人的认识中,中医已然退出,这一阵地成了西医的专长和天下。就此而论,中原大学的皮国立博士从细菌或者说抗菌入手,来探究近代中医的发展和中西医论争,正可谓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和要害。
国立兄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医疗史的研究,他成长于医疗史研究氛围十分浓郁的台湾史学界,并频繁往来于海峡两岸,是两岸中国医疗史乃至近代史领域中拥有广泛影响的中青年学者。近十多年来,国立兄笔耕不辍,成果丰硕。在我印象中,他应该是中国医疗史研究领域为数不多的最具学术活跃度的学者之一。他继以唐宗海为中心来探究近代中西医汇通之后,抓住这一关键议题来展开对中西医论争背景中近代中医演变的研究,不仅充分说明了他的勤奋和积极进取,更展现了他敏锐的学术眼光。
无论是中西医论争还是近代中医发展,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议题,要想就老议题说出新意趣来,抓住问题的要害、提出好问题是关键。国立兄希望从对细菌学说的应对入手,来展现和思考近代中医的“再正典化”过程,无论是选题还是立意都十分巧妙而有意义。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我的考量,大概不外乎以下两点:
首先,应得益于他对近代中医学人诸多论述的深入钻研。国立兄早年围绕着唐宗海,对近代特别是晚清中西医汇通学说有颇为深入的研究,后来大量研读了民国时期恽铁樵等诸多中医学人论著,正是这样系统细致的阅读,使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中医学人对西方医学的关注点从生理学转向了细菌学,从而促使他将此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其次,也源于他对中医的现代性拥有颇为清醒的认识。在很多人的认识中,中国医学是从中国这片土地起源和发展起来的治疗疾病的知识体系,从古到今是一脉相承、不断发展的。早在秦汉时期甚至更早,《黄帝内经》、《难经》和《伤寒论》等经典著作就已成形,并在当今的中医教育体系中仍为“活着的经典”,而且阴阳五行、虚实寒热、针刺艾灸甚至“辨证论治”等旧有的概念和方法也似乎古今一脉。故尽管中医知识古往今来时有发展,但根本上,其乃是一种本质性的存在,其本质早在先秦、秦汉时代就已经确定,后代的变化不过在其根本体系上做些修修补补而已。中医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瑰宝,而且还是中国唯一活着的“古代科学”。这样的看法,在当今中国医学史和中医学论著中甚为流行,甚至几为定论。既然中医是传统,是古今一脉的本质性存在,自然无所谓现代中医或中医的现代性了。
不过事实可能未必如此,我们不妨从现代有关中医的基本认识入手来做一剖析。现代说到中医,大家几乎都会毫不犹豫将“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视为中医的根本特征和优势,然而现有的研究已经雄辩地表明,“辨证论治”理论和方法与“整体观念”,虽然在近代以前的医学中不是全无踪影,但不仅很少有人论及,更无人将其视为中医学的根本特色和理论。1949年以后,受“西学中”和“大力发展中医药”等政策的影响和驱动,一批医界精英在“科学化”和“国学化”双重理念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在民国时期诸多论述的基础上,成功地构建了“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两大理论,不仅填补了因为抛却阴阳五行等而导致的中医核心理论的空缺,而且还构建了一个与西医不同的中医形象,并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与优越性。进而言之,以西医为参照对象而被视为传统的当下中医,若从中国医学自身的演进脉络来说,实为“现代”。当代中医乃是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渐被质疑甚至否定,以及西方医学的强势进入和日益迅猛的发展,一代代中医学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努力用现代的科学和学科思维,通过医学史钩沉和传统医学知识筛选,逐渐建构起来的一套现代知识体系。也就是说,中医并不是一种作为传统象征的本质性存在,也不是脱离中国历史文化而孤立存在并自足发展的,而是随着中国历史文化的变迁而不断演进的知识体系。
不用说,国立兄很清楚这些。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他才会提出近代中医“再正典化”的问题。围绕着“菌”、“气”、“伤寒”、“温病”等概念,通过对民国时期诸多以中医学人为主的文人论述的细致梳理,国立兄向我们展示了近代中医是如何消化西方细菌学说,并将部分理论和知识化入旧有概念之中的。在科学化、专业化的大潮中,诸多中医先贤们或出于生计的考虑,或因为自身的文化情感,或缘于民族的情怀,面对日渐强势的西方文明以及西方医学,奋力自救,最终使中医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具有了可以立足现代社会的现代性。对于民国乃至当代中医学人在科学化和专业化潮流中对中医的重新塑造,尽管今天不时会受到部分主张回到传统的中医人的批评,但必须说,这些成果无疑是时代文明和一代代中医知识精英智慧的结晶。而且在我看来,他们的努力总体上也是相当成功的,毫无疑问,中医在当代中国能够成为体制内与西医并存的医疗体系,他们的努力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还存在着种种的问题,并不尽如人意,但中医作为现代社会中的科技、专业和医疗体系,至少在形式和机制上,其学术的表达形式、知识的传承和教育方式以及医疗机构的运作模式等,都可谓已成功地融入现代社会。
尽管如此,若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却又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近代以来,中医在努力自救、不断追求自我发展的过程,也正是在与西医竞争中不断失势、主战阵地日渐退缩的过程,何以如此?个中的原因自然是纷繁复杂的,不过有个基本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西医在治疗感染性疾病上之所以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显然不是西医的理论有多么高深,道理有多么动人,而是因为在细菌学理论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发明了抗生素这一对付病菌的“魔弹”。反观近代以来诸多中医知识精英的论述,可以发现,他们将最大量的精力似乎用在如何使中医具有科学性和合法性,使其理论逻辑自洽、华丽动人,从而能得到政界和民众的支持而得以自存上,而比较少致力于提升具体的医疗技术。这一事实提醒我们,近代中医发展虽然成绩巨大,但方向是否有值得重新检讨之处呢?
国立兄虽然在书中并没有直接提及这些问题,但他在《自序》中言:“除了历史知识外,期待读者也能省思现代中医的发展与定位,不是为了与西医争胜,而在于治病济世、造福全人类。”实与吾心有戚戚焉!我和国立兄都是历史学出身,历史学无疑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但通过拜读他的文字,我时时能体会到他有一份发自内心的对中医的关注。这在往往被称为外史的医疗社会史学界的同仁中,可能是少数吧。正因如此,体会到这份我们共同的志趣,每每让我感到欣慰和鼓舞。应该也与这一情怀有关,近些年,我总在积极倡言医史研究要打破内外史的壁垒,实现内外史的融通。国立兄说法虽与我有所不同,主张探究“重层医史”,即希望通过“重层医史”的探讨,来实现医学学术和日常医疗社会探讨勾连和贯通,其旨趣大概也是一致的吧。
理想的阅读很大程度上乃是读者和作者心灵的沟通,正因为有这些心意相通之处,阅读该著,对我来说是种愉快的体验,不时产生的学术启益自令人欣喜,而常常感受到的意趣相投,更让人深感慰藉。故此,我实在没有理由不郑重向读者推荐这部兼学术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好书。不过与此同时,我还想说,学术研究是没有止境的远航,特别是对年轻的中国医疗史研究来说,更是如此。虽然我们可能已在已有基础上尽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远没有到可以停下来自我欣赏的程度。如果按中医学界一些学者或许有些严苛的要求来自省,我们的研究对于中医发展究竟带来怎样真正的启益?“重层医史”,究竟如何在日常生活和医疗实践的角度展现对医学知识的型塑?对如此等等的问题,显然,史学界年轻的中国医疗史研究恐怕一时还很难有底气给予满意的答案。这样的话,那我们又如何可以让别人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中国医学的核心地带了呢?
毫无疑问,我们念兹在兹的中国医疗史研究未来的路还很长,是以聊赘数语,一者向国立兄新著的出版致贺,二者也略陈学习心得,就教于国立兄及学界同仁,以期共同推动这一研究的蓬勃发展。
余新忠
2019年1月26日于津门寓所
自序 有“生命”的医疗史
中医和西医的会面、碰撞与汇通,是近代医学史无法回避的主题,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个人做学问之路,无甚可称述,在此仅表达一份幸运与一份感激,落笔数言,以示对读者之负责。
笔者自从攻读硕士班开始,即踏入“生命与医疗史”的研究领域,得以一窥中国医学之堂奥,分析它在近代碰到的挑战,并探索一代学人寻求出路之可能。晚清之时,中西医的碰撞主要在解剖与生理学上的争端;至民国之后,中西医则转而在细菌学和病理学上争胜。以后者牵涉到实际治疗和中国医学以“内科”伤寒学、温病学为主的核心理论体系,所以不论在疗效或学理上的争端,其牵涉之广、言论之激,皆超越前代。本书主轴,即为书写民国以来的疾病与医疗史,在整体细菌学上的争议。个人对中医学理本极有兴趣,虽无能行医济世,但总还能从历史学的角度,提出一些对中医发展的观察。在中西医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近代中医同西医在热病治疗学的较量上,完全没有屈居下风,值得读者省思。若是连“喊战”、“抗战”都没有资格,日子久了、特色暗淡了,那么中医的“生命”也将走向尽头。史事可鉴,研究中医者能不警醒乎?
近代中西医的博弈,起自晚清,最初多在解剖生理学内交手,学理上之争论实大于疗效上的争胜,应该说,中医疗法在当时仍有一定的优势。不过,进入20世纪初,西医在细菌论上取得重大突破,接连成立的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在防疫等卫生政策上全面向西医靠拢,而于教育政策上又处处限制中医发展。当时中西医博弈的焦点就在“废医案”的提出,1928年国民政府卫生部成立,根据该部组织法,旗下设立中央卫生委员会,以作为卫生决策的议决机关。当时担任委员者,无一具有中医背景。第一届委员会于1929年2月23日在南京召开,会议上以“中医妨碍全国医事卫生”为由,提出四项针对废除中医的提案,分别是《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统一医士登录办法》、《限定中医登记年限》和《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等,统称“废医案”。最后通过并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内容简单归纳即:不允许中医办学校,并取缔中医药相关之“非科学”新闻杂志,进而逐步取消中医执照登记,采取渐进手段来限制中医,最终达到完全消灭中医的目标。随后,上海等地的报纸首先揭露中央卫生委员会的会议内容,舆论一阵哗然。至3月17日,遂有上海中医协会组织,在上海举办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组织晋京请愿团,决定至南京中央政府各机关请愿,终于将“废医案”阻挡下来,赢得中医发展的一线生机。这是全国中医界的首次大团结,用各种力量和渠道去争取自身权益的重大运动,值得现代中医省思。
笔者以为,该运动实为“现代中医史的开端”。在此事件与运动发生之前,中西医之间的博弈或融通,不过是基于学术上的兴趣和文字讨论,采用与否端看中医个人的抉择;但此运动发生之后,中医界自晚清以来所尝试的组织学会、出版医报与串联团结、诉诸媒体舆论、冀求政治与法律上平等的诸般举措,一夕之间都变得“必要”。而学习西医要怎么学,如何科学化,中药疗效和实验步骤为何,中医知识体系如何转型以因应变局等问题,全部都成了中医在博弈中取得生存空间与持续发展的迫切要事。可以说此事件促使中医界迅速在各方面进行变革,以至于我们今日所认知的现代中医逐渐和传统中医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异与断裂。怎么处理传统中医理论、典籍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成了近百年中医史的主旋律。以史为鉴,我们正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从历史中我们得知中医现状与处境之由来。细菌理论既然是西医在20世纪初取得的最大成果,中医在这场博弈中当然要努力证实自身于对抗细菌、治疗传染病上的优势与技术。而这段历史恰恰揭示了,中国医学唯有不断变革创新、顺势转型,强化治病的技术,才能永不退潮流,在日益激烈的中西博弈中取得一席之地,此为近代中国医疗历史的重大启示。
在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思考上,近代史家,笔者最推崇吕思勉。吕氏低调而踏实,在学术上绽放之光芒虽不及傅斯年、顾颉刚等民国学人来得耀眼,但实际著述成果则远超多数民国学人。他更撰写《医籍知津》,成就了名著《中国医学源流论》的基础。吕氏曾言:“予于教学,夙反对今人所谓纯学术及为学术而学术等论调。何者?人能作实事者多,擅长理论者少,同一理论,从事实体验出者多,且较确实,从书本上得来者少,且易错误。历来理论之发明,皆先从事实上体验到,然后借书本以补经验之不足,增益佐证而完成之耳。”历史研究必与实际相结合,才能谈读史之用。吕氏更谓,历史若脱离实际生活,则为“戏论”,史家不可能对当代之事茫然无知,夜夜闭户读书,而最后有所得者,这是他对历史功用的实际认识。此数语即笔者经历的小幸运。作为中国医疗史研究主体之“中医”,不但仍持续存在,而且生机盎然,为多数历史陈迹、故纸学问中所难能可贵者,为探讨近代中国文化出路的最佳史学课题之一。此端也即笔者有求于读者的:除了历史知识外,期待读者也能省思现代中医的发展与定位,不是为与西医争胜,而在于治病济世、造福全人类。如此才可谓本书具有“生命”,乃中国医疗历史与文化所赋予的“生命”,在西方的挑战下,曲折碰撞、汇通新生,而依旧昂首阔步、独立自主之谓也。
最后,要表达一份感激。本书旧版,得诸位学界先进厚爱,依序由吕芳上、黄怡超、张恒鸿、张哲嘉、刘士永、苏奕彰等先生撰写序言。其他欲感谢之学界师长、中医同道、朋友,皆已见于旧版自序《一位史学工作者生活与研究的自剖》,此书不再重复。简体版新问世,蒙南开大学余新忠教授撰写新的推荐序,使本书增色不少。2006年,笔者第一次到大陆发表医史论文,就是受到余老师的邀请,此书于大陆问世,这份机缘此刻也显得特别有意义。书内除增添新的研究外,也新增了章节,并全面“瘦身”,尽量省去较为冗长的脚注,以便阅读更顺畅。终归文字简练有功,总算有些新意。最后感谢中华书局上海公司原总经理余佐赞先生、责任编辑吴艳红女士,在这段时间给予出版工作上的一切支持。他们对编辑工作之热情与选书之慧眼独具,是本书得以问世的重要催生者。
皮国立
2018年12月于中原大学
张仲景的《伤寒论》无疑是中国医学史上最为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这部向被视为众方之祖的医书,也多被看作是中国临床医学的开山之作。该著在宋以后,开始受到诸多医家的推崇而日渐正典化,到明清时期,伴随着张仲景医圣地位的确立,《伤寒论》也渐趋成为与儒学中的《四书》相类的医学经典。与此同时,明清特别是清代的医家,还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温病学说”。这一学说,在诸多的中国医学史论著中多被看作是明清医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以是观之,我们应该可以毫无疑义地认为,对“伤寒”、“温病”等疾病的认识和治疗,乃是中国传统医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这些疾病,按照今天的疾病分类,大体均可归之于外感性疾病,即由致病病原体导致的感染性疾病,也就是广义的传染病。按照当今医学的认识,这类病原体种类甚多,其中主要有细菌和病毒,不过在20世纪病毒被确认之前,学界和社会往往都以细菌名之。这也就是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对于由病菌引发的外感性疾病的诊治,不仅是中国医学关注的重点,也可谓是其特长。
然而吊诡的是,尽管近代以降,张仲景和《伤寒论》的地位不断地被确认和提升,一代代的中医学人也对“伤寒论”和“温病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做出了极其丰富的研究和建构。然而,放眼现实,却不得不承认,治疗由病菌引发的外感性疾病,早已不是中医的主战场,甚至在一般人的认识中,中医已然退出,这一阵地成了西医的专长和天下。就此而论,中原大学的皮国立博士从细菌或者说抗菌入手,来探究近代中医的发展和中西医论争,正可谓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和要害。
国立兄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医疗史的研究,他成长于医疗史研究氛围十分浓郁的台湾史学界,并频繁往来于海峡两岸,是两岸中国医疗史乃至近代史领域中拥有广泛影响的中青年学者。近十多年来,国立兄笔耕不辍,成果丰硕。在我印象中,他应该是中国医疗史研究领域为数不多的最具学术活跃度的学者之一。他继以唐宗海为中心来探究近代中西医汇通之后,抓住这一关键议题来展开对中西医论争背景中近代中医演变的研究,不仅充分说明了他的勤奋和积极进取,更展现了他敏锐的学术眼光。
无论是中西医论争还是近代中医发展,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议题,要想就老议题说出新意趣来,抓住问题的要害、提出好问题是关键。国立兄希望从对细菌学说的应对入手,来展现和思考近代中医的“再正典化”过程,无论是选题还是立意都十分巧妙而有意义。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我的考量,大概不外乎以下两点:
首先,应得益于他对近代中医学人诸多论述的深入钻研。国立兄早年围绕着唐宗海,对近代特别是晚清中西医汇通学说有颇为深入的研究,后来大量研读了民国时期恽铁樵等诸多中医学人论著,正是这样系统细致的阅读,使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中医学人对西方医学的关注点从生理学转向了细菌学,从而促使他将此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其次,也源于他对中医的现代性拥有颇为清醒的认识。在很多人的认识中,中国医学是从中国这片土地起源和发展起来的治疗疾病的知识体系,从古到今是一脉相承、不断发展的。早在秦汉时期甚至更早,《黄帝内经》、《难经》和《伤寒论》等经典著作就已成形,并在当今的中医教育体系中仍为“活着的经典”,而且阴阳五行、虚实寒热、针刺艾灸甚至“辨证论治”等旧有的概念和方法也似乎古今一脉。故尽管中医知识古往今来时有发展,但根本上,其乃是一种本质性的存在,其本质早在先秦、秦汉时代就已经确定,后代的变化不过在其根本体系上做些修修补补而已。中医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瑰宝,而且还是中国唯一活着的“古代科学”。这样的看法,在当今中国医学史和中医学论著中甚为流行,甚至几为定论。既然中医是传统,是古今一脉的本质性存在,自然无所谓现代中医或中医的现代性了。
不过事实可能未必如此,我们不妨从现代有关中医的基本认识入手来做一剖析。现代说到中医,大家几乎都会毫不犹豫将“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视为中医的根本特征和优势,然而现有的研究已经雄辩地表明,“辨证论治”理论和方法与“整体观念”,虽然在近代以前的医学中不是全无踪影,但不仅很少有人论及,更无人将其视为中医学的根本特色和理论。1949年以后,受“西学中”和“大力发展中医药”等政策的影响和驱动,一批医界精英在“科学化”和“国学化”双重理念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在民国时期诸多论述的基础上,成功地构建了“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两大理论,不仅填补了因为抛却阴阳五行等而导致的中医核心理论的空缺,而且还构建了一个与西医不同的中医形象,并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与优越性。进而言之,以西医为参照对象而被视为传统的当下中医,若从中国医学自身的演进脉络来说,实为“现代”。当代中医乃是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渐被质疑甚至否定,以及西方医学的强势进入和日益迅猛的发展,一代代中医学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努力用现代的科学和学科思维,通过医学史钩沉和传统医学知识筛选,逐渐建构起来的一套现代知识体系。也就是说,中医并不是一种作为传统象征的本质性存在,也不是脱离中国历史文化而孤立存在并自足发展的,而是随着中国历史文化的变迁而不断演进的知识体系。
不用说,国立兄很清楚这些。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他才会提出近代中医“再正典化”的问题。围绕着“菌”、“气”、“伤寒”、“温病”等概念,通过对民国时期诸多以中医学人为主的文人论述的细致梳理,国立兄向我们展示了近代中医是如何消化西方细菌学说,并将部分理论和知识化入旧有概念之中的。在科学化、专业化的大潮中,诸多中医先贤们或出于生计的考虑,或因为自身的文化情感,或缘于民族的情怀,面对日渐强势的西方文明以及西方医学,奋力自救,最终使中医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具有了可以立足现代社会的现代性。对于民国乃至当代中医学人在科学化和专业化潮流中对中医的重新塑造,尽管今天不时会受到部分主张回到传统的中医人的批评,但必须说,这些成果无疑是时代文明和一代代中医知识精英智慧的结晶。而且在我看来,他们的努力总体上也是相当成功的,毫无疑问,中医在当代中国能够成为体制内与西医并存的医疗体系,他们的努力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还存在着种种的问题,并不尽如人意,但中医作为现代社会中的科技、专业和医疗体系,至少在形式和机制上,其学术的表达形式、知识的传承和教育方式以及医疗机构的运作模式等,都可谓已成功地融入现代社会。
尽管如此,若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却又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近代以来,中医在努力自救、不断追求自我发展的过程,也正是在与西医竞争中不断失势、主战阵地日渐退缩的过程,何以如此?个中的原因自然是纷繁复杂的,不过有个基本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西医在治疗感染性疾病上之所以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显然不是西医的理论有多么高深,道理有多么动人,而是因为在细菌学理论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发明了抗生素这一对付病菌的“魔弹”。反观近代以来诸多中医知识精英的论述,可以发现,他们将最大量的精力似乎用在如何使中医具有科学性和合法性,使其理论逻辑自洽、华丽动人,从而能得到政界和民众的支持而得以自存上,而比较少致力于提升具体的医疗技术。这一事实提醒我们,近代中医发展虽然成绩巨大,但方向是否有值得重新检讨之处呢?
国立兄虽然在书中并没有直接提及这些问题,但他在《自序》中言:“除了历史知识外,期待读者也能省思现代中医的发展与定位,不是为了与西医争胜,而在于治病济世、造福全人类。”实与吾心有戚戚焉!我和国立兄都是历史学出身,历史学无疑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但通过拜读他的文字,我时时能体会到他有一份发自内心的对中医的关注。这在往往被称为外史的医疗社会史学界的同仁中,可能是少数吧。正因如此,体会到这份我们共同的志趣,每每让我感到欣慰和鼓舞。应该也与这一情怀有关,近些年,我总在积极倡言医史研究要打破内外史的壁垒,实现内外史的融通。国立兄说法虽与我有所不同,主张探究“重层医史”,即希望通过“重层医史”的探讨,来实现医学学术和日常医疗社会探讨勾连和贯通,其旨趣大概也是一致的吧。
理想的阅读很大程度上乃是读者和作者心灵的沟通,正因为有这些心意相通之处,阅读该著,对我来说是种愉快的体验,不时产生的学术启益自令人欣喜,而常常感受到的意趣相投,更让人深感慰藉。故此,我实在没有理由不郑重向读者推荐这部兼学术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好书。不过与此同时,我还想说,学术研究是没有止境的远航,特别是对年轻的中国医疗史研究来说,更是如此。虽然我们可能已在已有基础上尽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远没有到可以停下来自我欣赏的程度。如果按中医学界一些学者或许有些严苛的要求来自省,我们的研究对于中医发展究竟带来怎样真正的启益?“重层医史”,究竟如何在日常生活和医疗实践的角度展现对医学知识的型塑?对如此等等的问题,显然,史学界年轻的中国医疗史研究恐怕一时还很难有底气给予满意的答案。这样的话,那我们又如何可以让别人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中国医学的核心地带了呢?
毫无疑问,我们念兹在兹的中国医疗史研究未来的路还很长,是以聊赘数语,一者向国立兄新著的出版致贺,二者也略陈学习心得,就教于国立兄及学界同仁,以期共同推动这一研究的蓬勃发展。
余新忠
2019年1月26日于津门寓所
自序 有“生命”的医疗史
中医和西医的会面、碰撞与汇通,是近代医学史无法回避的主题,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个人做学问之路,无甚可称述,在此仅表达一份幸运与一份感激,落笔数言,以示对读者之负责。
笔者自从攻读硕士班开始,即踏入“生命与医疗史”的研究领域,得以一窥中国医学之堂奥,分析它在近代碰到的挑战,并探索一代学人寻求出路之可能。晚清之时,中西医的碰撞主要在解剖与生理学上的争端;至民国之后,中西医则转而在细菌学和病理学上争胜。以后者牵涉到实际治疗和中国医学以“内科”伤寒学、温病学为主的核心理论体系,所以不论在疗效或学理上的争端,其牵涉之广、言论之激,皆超越前代。本书主轴,即为书写民国以来的疾病与医疗史,在整体细菌学上的争议。个人对中医学理本极有兴趣,虽无能行医济世,但总还能从历史学的角度,提出一些对中医发展的观察。在中西医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近代中医同西医在热病治疗学的较量上,完全没有屈居下风,值得读者省思。若是连“喊战”、“抗战”都没有资格,日子久了、特色暗淡了,那么中医的“生命”也将走向尽头。史事可鉴,研究中医者能不警醒乎?
近代中西医的博弈,起自晚清,最初多在解剖生理学内交手,学理上之争论实大于疗效上的争胜,应该说,中医疗法在当时仍有一定的优势。不过,进入20世纪初,西医在细菌论上取得重大突破,接连成立的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在防疫等卫生政策上全面向西医靠拢,而于教育政策上又处处限制中医发展。当时中西医博弈的焦点就在“废医案”的提出,1928年国民政府卫生部成立,根据该部组织法,旗下设立中央卫生委员会,以作为卫生决策的议决机关。当时担任委员者,无一具有中医背景。第一届委员会于1929年2月23日在南京召开,会议上以“中医妨碍全国医事卫生”为由,提出四项针对废除中医的提案,分别是《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统一医士登录办法》、《限定中医登记年限》和《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等,统称“废医案”。最后通过并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内容简单归纳即:不允许中医办学校,并取缔中医药相关之“非科学”新闻杂志,进而逐步取消中医执照登记,采取渐进手段来限制中医,最终达到完全消灭中医的目标。随后,上海等地的报纸首先揭露中央卫生委员会的会议内容,舆论一阵哗然。至3月17日,遂有上海中医协会组织,在上海举办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组织晋京请愿团,决定至南京中央政府各机关请愿,终于将“废医案”阻挡下来,赢得中医发展的一线生机。这是全国中医界的首次大团结,用各种力量和渠道去争取自身权益的重大运动,值得现代中医省思。
笔者以为,该运动实为“现代中医史的开端”。在此事件与运动发生之前,中西医之间的博弈或融通,不过是基于学术上的兴趣和文字讨论,采用与否端看中医个人的抉择;但此运动发生之后,中医界自晚清以来所尝试的组织学会、出版医报与串联团结、诉诸媒体舆论、冀求政治与法律上平等的诸般举措,一夕之间都变得“必要”。而学习西医要怎么学,如何科学化,中药疗效和实验步骤为何,中医知识体系如何转型以因应变局等问题,全部都成了中医在博弈中取得生存空间与持续发展的迫切要事。可以说此事件促使中医界迅速在各方面进行变革,以至于我们今日所认知的现代中医逐渐和传统中医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异与断裂。怎么处理传统中医理论、典籍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成了近百年中医史的主旋律。以史为鉴,我们正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从历史中我们得知中医现状与处境之由来。细菌理论既然是西医在20世纪初取得的最大成果,中医在这场博弈中当然要努力证实自身于对抗细菌、治疗传染病上的优势与技术。而这段历史恰恰揭示了,中国医学唯有不断变革创新、顺势转型,强化治病的技术,才能永不退潮流,在日益激烈的中西博弈中取得一席之地,此为近代中国医疗历史的重大启示。
在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思考上,近代史家,笔者最推崇吕思勉。吕氏低调而踏实,在学术上绽放之光芒虽不及傅斯年、顾颉刚等民国学人来得耀眼,但实际著述成果则远超多数民国学人。他更撰写《医籍知津》,成就了名著《中国医学源流论》的基础。吕氏曾言:“予于教学,夙反对今人所谓纯学术及为学术而学术等论调。何者?人能作实事者多,擅长理论者少,同一理论,从事实体验出者多,且较确实,从书本上得来者少,且易错误。历来理论之发明,皆先从事实上体验到,然后借书本以补经验之不足,增益佐证而完成之耳。”历史研究必与实际相结合,才能谈读史之用。吕氏更谓,历史若脱离实际生活,则为“戏论”,史家不可能对当代之事茫然无知,夜夜闭户读书,而最后有所得者,这是他对历史功用的实际认识。此数语即笔者经历的小幸运。作为中国医疗史研究主体之“中医”,不但仍持续存在,而且生机盎然,为多数历史陈迹、故纸学问中所难能可贵者,为探讨近代中国文化出路的最佳史学课题之一。此端也即笔者有求于读者的:除了历史知识外,期待读者也能省思现代中医的发展与定位,不是为与西医争胜,而在于治病济世、造福全人类。如此才可谓本书具有“生命”,乃中国医疗历史与文化所赋予的“生命”,在西方的挑战下,曲折碰撞、汇通新生,而依旧昂首阔步、独立自主之谓也。
最后,要表达一份感激。本书旧版,得诸位学界先进厚爱,依序由吕芳上、黄怡超、张恒鸿、张哲嘉、刘士永、苏奕彰等先生撰写序言。其他欲感谢之学界师长、中医同道、朋友,皆已见于旧版自序《一位史学工作者生活与研究的自剖》,此书不再重复。简体版新问世,蒙南开大学余新忠教授撰写新的推荐序,使本书增色不少。2006年,笔者第一次到大陆发表医史论文,就是受到余老师的邀请,此书于大陆问世,这份机缘此刻也显得特别有意义。书内除增添新的研究外,也新增了章节,并全面“瘦身”,尽量省去较为冗长的脚注,以便阅读更顺畅。终归文字简练有功,总算有些新意。最后感谢中华书局上海公司原总经理余佐赞先生、责任编辑吴艳红女士,在这段时间给予出版工作上的一切支持。他们对编辑工作之热情与选书之慧眼独具,是本书得以问世的重要催生者。
皮国立
2018年12月于中原大学
精彩书摘
第二节 西风又东风——传统医学视角的文化史
中医杨志一在1936年说:“大凡学术之成立,历久而不败者,必有其真实之价值在。”近代中国许多传统学门都有真价值,如何保持那份价值,则困难重重。即如本书所言“再正典化”现象,也不是顺理成章的趋势,其背后历程其实非常艰苦。当1929年“废医案”出炉时,一位叫雷济的中医上书畅言中医不能骤废的理由,结果卫生部的回函,打了他一个大巴掌。
原呈(文)所称“中医谓致病之因,由于邪气,西医谓致病之因,由于细菌”,已属一知半解之谈,竟谓有邪气方有细菌,无邪气必无细菌,尤属错误,毫无生物学之常识。至原呈所举肉类之试验,不过证明蒸熟之肉,虽经消毒,肉类本身或盛肉之器具若未完全灭菌,则未经杀死之细菌,仍能发育,不足以证明邪气之存在。也因该医只知有“细菌”两字而已,对于细菌学实在毫无认识。按诸科学医理疾病之原因,甚为复杂,亦非全由微生物而起,而微生物之种类亦甚夥,并非全可以致病,该医对于此种常识既不明了,且立论又只就细菌之发生一点致辩,实属满纸空谈,毫无价值,拟请无庸置议。
这则回函,等于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认定与细菌学相对的“气论”是胡说八道的,至于微生物学之复杂,也不是中医空谈即可明了的学问。文化界的例子,书内已列举许多,最后仅补充陈独秀的说法。他认为现代中国人要脱离蒙昧时代,就必须科学与人权并重,其中关于科学有谓:
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
不论从国家法令之合法性,还是科学发展之合理性,其矛头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中医气论之误谬。近代中医面临是坚守自身传统理论,还是选择一脚踏入西方医学领域,甩开气论?中医只能退让,丢掉气论吗?当时中医之两难,颇似民初知识分子在许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摇摆与“两歧性”。钱穆曾说:“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恐怕在那个时代要立刻做出一面倒向西方文化的决定,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对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而言。周明之指出胡适在许多方面的摇摆是因为他面对西方价值时的自卑或担忧,促使他回到传统中,去找寻作为中国人的自尊。周给这样的心态取了一个名字:“旧与新的内在同化”——他们无法完全抛弃传统而远眺西方,而其“忽而西忽而东”的摇摆立场,其实是在为现代性找一个出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中医除了合法与科学外,还承载一种传统文化的深层性格。这对中医而言,在科学化的进程中是不利的,但在当时,好坏还未可尽知。
民国中医继承的是一种根据古典医籍内容与理论来理解的身体观,要创造一个过去所没有的“无中生有”的论述,必须是在阅读细菌学的相关书籍后,根据医者过往学习古典医学的知识,展开一种具有解释力的新诠释;近代日本汉医所做的,也正是这些,汤本在论述中药杀菌的可能性时,其灵感除来自日本汉药学研究,还来自中国古代医学经典。对西医而言,在科技进步迅速的情况下,“经典”不可能永远存在,古医书不须去反复阅读、注解,是以就文化而论,西方医学科学所承载之过往传统不如中医来得深沉。近代西医靠实验来研究细菌,而中医则靠古典医学来理解“六气”知识,此为根本上的不同。“气”代表物质的性质,如食物的性味与禁忌,调养的方式与空间特性,等等。了解这套知识,对认识中国式的疾病论述有很大的帮助,且具有贴近身体感的日常实用性质,不单是虚无缥缈的哲学论述,实有似西方科学之基本“元素”。虽然,也有医者主张废除“气化”,用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医典籍,但其方法仍是以中医文献中的治疗症候与疗效,来辨别药理与治疗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整理研究方法,很难不去碰触“气”的问题。章太炎曾说:“医者之妙,喻如行师,运用操舍,以一心察微而得之,此非所谓哲学也,谓其变化无方之至耳。”唐慎轩于1936年即称章太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非其真积力久,曷克臻此”。医学是变化的道理,必须切身体会,理论不过是入门,具体理则则需由实际治疗经验验证。故近代中医最担心采行西医论述,就要接受西医与细菌学之背后一整套技术操作与解释疾病的知识体系,包括运用西方教科书等。那么,古典医学理论又能保存多少,故中医颇感窒碍难行。
在近代学术转型的探索中,任何一学科,包括医学在内,其实都要面临一种“双向反省”,即一方面对新学说或西学的回应,同时,也回头思考传统学术在新时代的定位,透过西方科学重现古典医书的价值,即四川罗燮元曾赞叹的:“我国埋没于数千年来故纸堆中之病症,得以大白于天下,不亦大可快哉!”虽然真正之整理,要到1950年代之后,然民国时已可见其大致思想端倪与发展趋势,这是百年中医史中的重要议题,已在中医学术的各个领域开花,今后皆可持续探索。而书中恽铁樵的例子即颇能说明中医传统派的态度,显示了中医在细菌、病名、自身学术之间的一种尴尬与紧张的关系。他坚持以六气、四时或辨证的立场,来回应中医即将失去定义病名权力的危机,但实际上他又无法逃避“认识细菌说”的时代压力。故总体归纳而言:恽能做的就是忽略细菌说的本体,以《伤寒论》为基调来找出任何统一、定义疾病的可能。而各种“杀菌”法,其实也是从各种药物学和经典中启发而来,如“发汗”可能偏重伤寒的经典,“解毒”则偏重温病或瘟疫论述。民国中医的热病论述实不只主“杀菌”的意义,不然即无法解释中医为什么没有走向发展出杀菌药,或是不往这个方面做治疗的再思考。除了没有实验室、科学方法等外,更重要的是,中医即便有杀菌药,也应谨守气论的界限,因为中医乃依寒热之“气”来对证治疗,而非对菌治疗的一种医学。所以,也不得不说,近代中医基于“气论”与身体观的完整,对于西方细菌学是采用一种讨论、反面论证与高度选择性接纳的态度。以西医的科学来研究中医,确实会让中医过于西医化,这也是民国中医“中医西化,则不复为中医”的疑虑。
故研究近代医史不能只以新旧或科不科学来思索西医与中医。现代中医,不断采用西医的疾病语言,但在课堂上却仍学习古代经典。他们读《伤寒论》,却不太和病人谈“伤寒”,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何云鹤说:“1929年章太炎办上海国医学院,那是中国第一所正式采取现代医学作为基础的中医学校,院中的课程由陆渊雷厘订,基础医学像生物、化学、解剖、生理,都采用现代医学,应用各科则以中医原有的为主,并且侧重《伤寒论》的经验。”大概现代中医基础课程也如此。1935年苏州国医学校的课程,甚至三年的修业期限,西医细菌、解剖学在第一年必修,中医内科则从二年级开始,并加重课程时数,此已开“先西后中”修业模式之先河;只是,经验需用于实际临床,而当日应用不取西医杀菌、外科之技术,此乃奠定现代中医之学术性格。即使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的影响,近代学科的“传统”边界,鲜有像中医那样保持完整的。本研究具有相当实际的意义与功能,我们要不断提醒现代中医:“历代圣贤智慧、经典”并不是每个民国医者都能理解的;回顾这些资产时,不能忘记很多中医对它们是非常陌生的,所以探讨这些历史,不只是历史意义,还有现实疗治的新启发。研读与研究医史文献,谁曰不可温古知新、创新思想?
近代中医史有趣之处也正在此。近代中国学术的“西化”已不用多谈,这个旧框架将阻挡我们观看近代中国史的全貌,因为它只有单一视角而已。很多人也许会质疑,这是不是一种“反科学”的立场?站在历史研究上,本来就不能只有一种单线论述,就像高彦颐(Dorothy Ko)提出的突破“五四史观”框架一样,作者的立场同为: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中医科不科学,或是中医为什么不科学的“五四史观”中,我们永远不会发现中医在近代的多元文化史以及中医在近代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可行性。而即便我们探究了受西医影响的部分,也无法得知当日中医对传统做了什么样的保护与妥协。何况对多数中国人来说,生活不是只有科学,而是一种自然的文化土壤,文化与历史不会只有单线发展。
虽然“科学”占据了民国知识界转型的主体,但“传统”之力量反从因外国侵略而对自身文化自卑兼自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真积力久,渐渐显现真实价值。钱穆曾批判西方科学几近“尽物性而损及人性”,可能和汤本的试管等同人体说类似。毛泽东在1957年曾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毛泽东认为当时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大好,可以压过西方的帝国主义,大概是希望中国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不受西方干扰和打压。在那一代领导人的心中,科学固然重要,但传统一样不可以抛弃,如蒋介石谓:“希望各位不仅是注意新的科学与学问,并且还要注重中国旧日的好学问,中国的旧书里学问很是渊博。” “从前不注意我们固有的文化,只知道拿外国的东西来学,忘掉了自己的根本,失却了自己固有的德行和精神,所以不能救国,不能完成革命事业。现在我们若是不早觉悟,照这样末的过下去,简直会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大概可以体现这种担忧传统文化丧失的关怀。20世纪30年代后的中医,颇能抓住民族主义的潮流,借由“文艺复兴、民族复兴”的潮流,搭上传统学术更新自主的列车,这种倾向是治近代医史者不能忽略的。
一个具“现代性”的中国将被带往何方,近百年来一直是大家寻求解答的一个问题。曾由中医治愈伤寒病的钱穆说:“中国文化是一向偏重在人文科学的,他注重具体的综括,不注重抽象的推概。惟其注重综括,所以常留着余地,好容新的事象与新的物变之随时参加。中国人一向心习之长处在此,所以能宽廓,能圆融,能吸收,能变通。若我们认为人文科学演进可以利用自然科学,可以驾驭自然科学,则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容得进近代西方之科学文明,这是不成问题的。不仅可以容受,应该还能融化能开新。这是我们对于面临的最近中国新文化时期之前途的希望。”文人之关怀如是,近代国家领导人也应对将中国带往何方的问题做出立场宣示,故蒋介石谈及对“国医”的期待时说:“中央国医馆昨日在京成立,此为中国医药由整理而进步之要事,吾顾其努力,实下功夫也。”毛泽东则谓:“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些话恐怕其大背景都不离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内向关怀,放在长期的历史来看,不见得只有科学意义在里面。这种科技要吹西风,文化要吹东风的论调,应是关心中国历史发展的学者都可接纳的中和之论。
就文化的角度来看,传统中国医书众多,怎么整理、用何种标准,还可以细论,尚待时间去证明。中医张国华说:
我国医道,由来尚矣。乃人所不满意者,谓中医学术一症各是其说,一方互相攻讦,不若西医之学有统系。今欲改进中医,诚非急谋有统系不可,然而统系亦岂易谋哉?然而所以难谋统系者,亦自有故。盖形上为道,形下为器,器粗而道精。中医之道,形上之道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所以悬殊,西医但求形质,中医深究气化,此西医统系易,而中医统系所以难也。然则中医竟不能统系乎?曰:亦惟先编一种有统系之医学,后可渐望有统系之学术,其道以《本经》及《内》、《难》、《金匮》为根据,至各种外感应宗何家,诸凡内伤应遵何氏,各科杂证应各采集何书,均须从长计议。撷其精华,去其糟粕,注释宜取简明切要,总使各科俱无遗憾,规定一种有统系之医学,俾后学可奉为圭臬,简练揣摩,拟定名曰医统集成,昭告天下,永以此为医学必由之正宗。
西医重形质而中医重气化,是以中医在整理学术方面,“气”的知识所涉及的问题最多、最复杂,也最难有统一的论点,但张认为还是必须从传统医籍出发来做整理。时逸人谓:“我国古代对于霍乱、痘疮,虽流传甚久,治疗方法多各一其说,不能划一;白喉、赤痢、疟疾、斑疹伤寒、猩红热等症状及治法,亦复诸说纷纭,不能一致;肠热症、回归热,古书中虽有类似记载,但名称未曾确定,治法尤多紊乱;鼠疫、脑膜炎,古本医书付之缺如,皆有汇集整理编订之必要。”这就是近代中医在外感热病学说内的最大挑战。那些埋没于数千年来故纸堆中之病症与疗法,如何加以好好研究,是近代中医乃至未来中医可以细细思量的课题。
民国学人与医者的意见,除了“废中医”外,本书完整关切了中医另一方面的想法。章太炎曾于大病一场后说:“余时少年锐进,不甚求道术,取医经视之,亦莫能辨其条理。中岁屡历忧患,始然痛求大乘教典,旁通老庄。晚岁更涉二程、陈、王师说,甚善之。功成屏居,岁岁逢天行疫疠,旦暮不能自保,于医经亦勤求之矣。”章氏对西方学术也有所涉猎,他晚年从自身实践与整个文化着手,在医学研究的路上看见医经之本。章视医学经典为个人读书体会所达到的一种境界,从读书到临证,而不是从摇试管、看显微镜开始训练。但是,基本上“汇通”还是近代中医走的路子。另外,钱穆说中国人具有“中和”性格,吸收西方科学而无损于传统文化,近代中医的历程可说是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个观点。王汎森对近代的传统与反传统思想有很多有见地的论述,他认为“守旧”和“复古”是两个不同的思想趋向,前者只是单纯效忠当前传统,而近代中医所谓的“复古”,则是跨越、扬弃更纯粹的传统,实蓄积大量的改革动能。故民国中医不可避免地要与西方文化汇通,绝不能用一种文化自大的观点来排斥一切西方的影响。所以讲“传统”、“复古”也未必一定和“西化”冲突,其实两者是互为影响的,传统的学问本已不免加入西方的某些元素。章太炎曾总结中西医各自的长处:“脏腑血脉之形,昔人初尝解剖而不能得其实,此当以西医为审。”“脏腑锢病,则西医愈于中医。”“中医之胜于西医者,大抵伤寒为独盛。”可见中西医相较,热病学仍有其价值,而当日中医也并非全带着一种自以为是的文化藩篱。“细菌”为贯通西医病理学的一门学问,而“气”则是贯通中医学的另一门学问,在还没有找到真正可以让中西医双方满意的汇通方式时,西医大唱废医,而中医当然只能固守古典医书构筑起的疗效与文化之防线。
(摘自《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结论”第二节,注释省略)
中医杨志一在1936年说:“大凡学术之成立,历久而不败者,必有其真实之价值在。”近代中国许多传统学门都有真价值,如何保持那份价值,则困难重重。即如本书所言“再正典化”现象,也不是顺理成章的趋势,其背后历程其实非常艰苦。当1929年“废医案”出炉时,一位叫雷济的中医上书畅言中医不能骤废的理由,结果卫生部的回函,打了他一个大巴掌。
原呈(文)所称“中医谓致病之因,由于邪气,西医谓致病之因,由于细菌”,已属一知半解之谈,竟谓有邪气方有细菌,无邪气必无细菌,尤属错误,毫无生物学之常识。至原呈所举肉类之试验,不过证明蒸熟之肉,虽经消毒,肉类本身或盛肉之器具若未完全灭菌,则未经杀死之细菌,仍能发育,不足以证明邪气之存在。也因该医只知有“细菌”两字而已,对于细菌学实在毫无认识。按诸科学医理疾病之原因,甚为复杂,亦非全由微生物而起,而微生物之种类亦甚夥,并非全可以致病,该医对于此种常识既不明了,且立论又只就细菌之发生一点致辩,实属满纸空谈,毫无价值,拟请无庸置议。
这则回函,等于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认定与细菌学相对的“气论”是胡说八道的,至于微生物学之复杂,也不是中医空谈即可明了的学问。文化界的例子,书内已列举许多,最后仅补充陈独秀的说法。他认为现代中国人要脱离蒙昧时代,就必须科学与人权并重,其中关于科学有谓:
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
不论从国家法令之合法性,还是科学发展之合理性,其矛头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中医气论之误谬。近代中医面临是坚守自身传统理论,还是选择一脚踏入西方医学领域,甩开气论?中医只能退让,丢掉气论吗?当时中医之两难,颇似民初知识分子在许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摇摆与“两歧性”。钱穆曾说:“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恐怕在那个时代要立刻做出一面倒向西方文化的决定,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对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而言。周明之指出胡适在许多方面的摇摆是因为他面对西方价值时的自卑或担忧,促使他回到传统中,去找寻作为中国人的自尊。周给这样的心态取了一个名字:“旧与新的内在同化”——他们无法完全抛弃传统而远眺西方,而其“忽而西忽而东”的摇摆立场,其实是在为现代性找一个出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中医除了合法与科学外,还承载一种传统文化的深层性格。这对中医而言,在科学化的进程中是不利的,但在当时,好坏还未可尽知。
民国中医继承的是一种根据古典医籍内容与理论来理解的身体观,要创造一个过去所没有的“无中生有”的论述,必须是在阅读细菌学的相关书籍后,根据医者过往学习古典医学的知识,展开一种具有解释力的新诠释;近代日本汉医所做的,也正是这些,汤本在论述中药杀菌的可能性时,其灵感除来自日本汉药学研究,还来自中国古代医学经典。对西医而言,在科技进步迅速的情况下,“经典”不可能永远存在,古医书不须去反复阅读、注解,是以就文化而论,西方医学科学所承载之过往传统不如中医来得深沉。近代西医靠实验来研究细菌,而中医则靠古典医学来理解“六气”知识,此为根本上的不同。“气”代表物质的性质,如食物的性味与禁忌,调养的方式与空间特性,等等。了解这套知识,对认识中国式的疾病论述有很大的帮助,且具有贴近身体感的日常实用性质,不单是虚无缥缈的哲学论述,实有似西方科学之基本“元素”。虽然,也有医者主张废除“气化”,用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医典籍,但其方法仍是以中医文献中的治疗症候与疗效,来辨别药理与治疗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整理研究方法,很难不去碰触“气”的问题。章太炎曾说:“医者之妙,喻如行师,运用操舍,以一心察微而得之,此非所谓哲学也,谓其变化无方之至耳。”唐慎轩于1936年即称章太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非其真积力久,曷克臻此”。医学是变化的道理,必须切身体会,理论不过是入门,具体理则则需由实际治疗经验验证。故近代中医最担心采行西医论述,就要接受西医与细菌学之背后一整套技术操作与解释疾病的知识体系,包括运用西方教科书等。那么,古典医学理论又能保存多少,故中医颇感窒碍难行。
在近代学术转型的探索中,任何一学科,包括医学在内,其实都要面临一种“双向反省”,即一方面对新学说或西学的回应,同时,也回头思考传统学术在新时代的定位,透过西方科学重现古典医书的价值,即四川罗燮元曾赞叹的:“我国埋没于数千年来故纸堆中之病症,得以大白于天下,不亦大可快哉!”虽然真正之整理,要到1950年代之后,然民国时已可见其大致思想端倪与发展趋势,这是百年中医史中的重要议题,已在中医学术的各个领域开花,今后皆可持续探索。而书中恽铁樵的例子即颇能说明中医传统派的态度,显示了中医在细菌、病名、自身学术之间的一种尴尬与紧张的关系。他坚持以六气、四时或辨证的立场,来回应中医即将失去定义病名权力的危机,但实际上他又无法逃避“认识细菌说”的时代压力。故总体归纳而言:恽能做的就是忽略细菌说的本体,以《伤寒论》为基调来找出任何统一、定义疾病的可能。而各种“杀菌”法,其实也是从各种药物学和经典中启发而来,如“发汗”可能偏重伤寒的经典,“解毒”则偏重温病或瘟疫论述。民国中医的热病论述实不只主“杀菌”的意义,不然即无法解释中医为什么没有走向发展出杀菌药,或是不往这个方面做治疗的再思考。除了没有实验室、科学方法等外,更重要的是,中医即便有杀菌药,也应谨守气论的界限,因为中医乃依寒热之“气”来对证治疗,而非对菌治疗的一种医学。所以,也不得不说,近代中医基于“气论”与身体观的完整,对于西方细菌学是采用一种讨论、反面论证与高度选择性接纳的态度。以西医的科学来研究中医,确实会让中医过于西医化,这也是民国中医“中医西化,则不复为中医”的疑虑。
故研究近代医史不能只以新旧或科不科学来思索西医与中医。现代中医,不断采用西医的疾病语言,但在课堂上却仍学习古代经典。他们读《伤寒论》,却不太和病人谈“伤寒”,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何云鹤说:“1929年章太炎办上海国医学院,那是中国第一所正式采取现代医学作为基础的中医学校,院中的课程由陆渊雷厘订,基础医学像生物、化学、解剖、生理,都采用现代医学,应用各科则以中医原有的为主,并且侧重《伤寒论》的经验。”大概现代中医基础课程也如此。1935年苏州国医学校的课程,甚至三年的修业期限,西医细菌、解剖学在第一年必修,中医内科则从二年级开始,并加重课程时数,此已开“先西后中”修业模式之先河;只是,经验需用于实际临床,而当日应用不取西医杀菌、外科之技术,此乃奠定现代中医之学术性格。即使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的影响,近代学科的“传统”边界,鲜有像中医那样保持完整的。本研究具有相当实际的意义与功能,我们要不断提醒现代中医:“历代圣贤智慧、经典”并不是每个民国医者都能理解的;回顾这些资产时,不能忘记很多中医对它们是非常陌生的,所以探讨这些历史,不只是历史意义,还有现实疗治的新启发。研读与研究医史文献,谁曰不可温古知新、创新思想?
近代中医史有趣之处也正在此。近代中国学术的“西化”已不用多谈,这个旧框架将阻挡我们观看近代中国史的全貌,因为它只有单一视角而已。很多人也许会质疑,这是不是一种“反科学”的立场?站在历史研究上,本来就不能只有一种单线论述,就像高彦颐(Dorothy Ko)提出的突破“五四史观”框架一样,作者的立场同为: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中医科不科学,或是中医为什么不科学的“五四史观”中,我们永远不会发现中医在近代的多元文化史以及中医在近代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可行性。而即便我们探究了受西医影响的部分,也无法得知当日中医对传统做了什么样的保护与妥协。何况对多数中国人来说,生活不是只有科学,而是一种自然的文化土壤,文化与历史不会只有单线发展。
虽然“科学”占据了民国知识界转型的主体,但“传统”之力量反从因外国侵略而对自身文化自卑兼自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真积力久,渐渐显现真实价值。钱穆曾批判西方科学几近“尽物性而损及人性”,可能和汤本的试管等同人体说类似。毛泽东在1957年曾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毛泽东认为当时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大好,可以压过西方的帝国主义,大概是希望中国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不受西方干扰和打压。在那一代领导人的心中,科学固然重要,但传统一样不可以抛弃,如蒋介石谓:“希望各位不仅是注意新的科学与学问,并且还要注重中国旧日的好学问,中国的旧书里学问很是渊博。” “从前不注意我们固有的文化,只知道拿外国的东西来学,忘掉了自己的根本,失却了自己固有的德行和精神,所以不能救国,不能完成革命事业。现在我们若是不早觉悟,照这样末的过下去,简直会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大概可以体现这种担忧传统文化丧失的关怀。20世纪30年代后的中医,颇能抓住民族主义的潮流,借由“文艺复兴、民族复兴”的潮流,搭上传统学术更新自主的列车,这种倾向是治近代医史者不能忽略的。
一个具“现代性”的中国将被带往何方,近百年来一直是大家寻求解答的一个问题。曾由中医治愈伤寒病的钱穆说:“中国文化是一向偏重在人文科学的,他注重具体的综括,不注重抽象的推概。惟其注重综括,所以常留着余地,好容新的事象与新的物变之随时参加。中国人一向心习之长处在此,所以能宽廓,能圆融,能吸收,能变通。若我们认为人文科学演进可以利用自然科学,可以驾驭自然科学,则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容得进近代西方之科学文明,这是不成问题的。不仅可以容受,应该还能融化能开新。这是我们对于面临的最近中国新文化时期之前途的希望。”文人之关怀如是,近代国家领导人也应对将中国带往何方的问题做出立场宣示,故蒋介石谈及对“国医”的期待时说:“中央国医馆昨日在京成立,此为中国医药由整理而进步之要事,吾顾其努力,实下功夫也。”毛泽东则谓:“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些话恐怕其大背景都不离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内向关怀,放在长期的历史来看,不见得只有科学意义在里面。这种科技要吹西风,文化要吹东风的论调,应是关心中国历史发展的学者都可接纳的中和之论。
就文化的角度来看,传统中国医书众多,怎么整理、用何种标准,还可以细论,尚待时间去证明。中医张国华说:
我国医道,由来尚矣。乃人所不满意者,谓中医学术一症各是其说,一方互相攻讦,不若西医之学有统系。今欲改进中医,诚非急谋有统系不可,然而统系亦岂易谋哉?然而所以难谋统系者,亦自有故。盖形上为道,形下为器,器粗而道精。中医之道,形上之道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所以悬殊,西医但求形质,中医深究气化,此西医统系易,而中医统系所以难也。然则中医竟不能统系乎?曰:亦惟先编一种有统系之医学,后可渐望有统系之学术,其道以《本经》及《内》、《难》、《金匮》为根据,至各种外感应宗何家,诸凡内伤应遵何氏,各科杂证应各采集何书,均须从长计议。撷其精华,去其糟粕,注释宜取简明切要,总使各科俱无遗憾,规定一种有统系之医学,俾后学可奉为圭臬,简练揣摩,拟定名曰医统集成,昭告天下,永以此为医学必由之正宗。
西医重形质而中医重气化,是以中医在整理学术方面,“气”的知识所涉及的问题最多、最复杂,也最难有统一的论点,但张认为还是必须从传统医籍出发来做整理。时逸人谓:“我国古代对于霍乱、痘疮,虽流传甚久,治疗方法多各一其说,不能划一;白喉、赤痢、疟疾、斑疹伤寒、猩红热等症状及治法,亦复诸说纷纭,不能一致;肠热症、回归热,古书中虽有类似记载,但名称未曾确定,治法尤多紊乱;鼠疫、脑膜炎,古本医书付之缺如,皆有汇集整理编订之必要。”这就是近代中医在外感热病学说内的最大挑战。那些埋没于数千年来故纸堆中之病症与疗法,如何加以好好研究,是近代中医乃至未来中医可以细细思量的课题。
民国学人与医者的意见,除了“废中医”外,本书完整关切了中医另一方面的想法。章太炎曾于大病一场后说:“余时少年锐进,不甚求道术,取医经视之,亦莫能辨其条理。中岁屡历忧患,始然痛求大乘教典,旁通老庄。晚岁更涉二程、陈、王师说,甚善之。功成屏居,岁岁逢天行疫疠,旦暮不能自保,于医经亦勤求之矣。”章氏对西方学术也有所涉猎,他晚年从自身实践与整个文化着手,在医学研究的路上看见医经之本。章视医学经典为个人读书体会所达到的一种境界,从读书到临证,而不是从摇试管、看显微镜开始训练。但是,基本上“汇通”还是近代中医走的路子。另外,钱穆说中国人具有“中和”性格,吸收西方科学而无损于传统文化,近代中医的历程可说是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个观点。王汎森对近代的传统与反传统思想有很多有见地的论述,他认为“守旧”和“复古”是两个不同的思想趋向,前者只是单纯效忠当前传统,而近代中医所谓的“复古”,则是跨越、扬弃更纯粹的传统,实蓄积大量的改革动能。故民国中医不可避免地要与西方文化汇通,绝不能用一种文化自大的观点来排斥一切西方的影响。所以讲“传统”、“复古”也未必一定和“西化”冲突,其实两者是互为影响的,传统的学问本已不免加入西方的某些元素。章太炎曾总结中西医各自的长处:“脏腑血脉之形,昔人初尝解剖而不能得其实,此当以西医为审。”“脏腑锢病,则西医愈于中医。”“中医之胜于西医者,大抵伤寒为独盛。”可见中西医相较,热病学仍有其价值,而当日中医也并非全带着一种自以为是的文化藩篱。“细菌”为贯通西医病理学的一门学问,而“气”则是贯通中医学的另一门学问,在还没有找到真正可以让中西医双方满意的汇通方式时,西医大唱废医,而中医当然只能固守古典医书构筑起的疗效与文化之防线。
(摘自《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结论”第二节,注释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