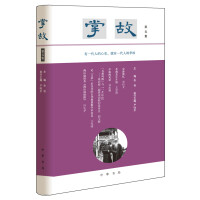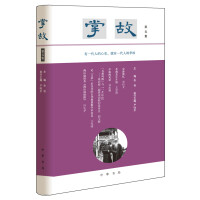1 交游漫忆/刘衍文
余与安持相见较频,友朋相聚,翁语独多,谈清末民初胜流掌故,滔滔不绝,几不容人置喙。惜其操平湖口音,且语速极快,十仅能了其五六耳,不若其身后所刊之《安持人物琐忆》之明晰也。谈及多人,一皆蔽之曰“好色”,而自承亦有“寡人之疾”。
12 季海先生片谈(上)/王学雷
在佩诤先生的笔下,只描述了季海先生一人的性格,显得十分突兀:朱学浩字季海,善音韵,性孤僻。寥寥十二字,就把他这位小师弟勾画了出来。这不正说明季海先生的性格实在是太强、太显眼了?
27 由“遗世独立,与天为徒”引起的追忆——与程千帆先生的相识相处/陈美林
岂知接手不及一月,便有一位党员助教来舍间,不容商量地让我交出唐老给我的材料,“助手”一职由他来当,并说是“领导”决定。我不得不交出唐老给我的几页活页纸。我向唐老汇报,唐老并不知情,在那种氛围下,唐老只能沉默。
44 怀念胡宛春、王驾吾二先生/雪 克
有次留宿农家,应门者为女主人,驾公开口就称“老板娘”,当场开了他的批斗会。事后,先生语我:“以何称呼为是?”自忖:“老板娘”实属不当,乃资产阶级思想之体现。称“房东”也未必有当,我辈留宿并非租客,而且白住不付分文,如果人家是贫下中农,岂非混淆了阶级界限?称“同志”则更荒唐,我等乃“牛鬼”身份,称他人和自己是“同志”,是何居心!
49 忆张大壮生平/樊伯炎遗稿 樊愉整理
原来湖帆手里也有几帧南田花卉册页,一对之下原是一时所作,是后人把它分成两册的,吴大为庆快。后虚斋告其樱桃实为大壮所补,吴不仅不以为愠,反而盛赞大壮之艺高,因传为佳话。
60 记黄永年先生/王培军
杨先生也是吕思勉的学生,算来是黄先生的同门,而同门之间互相火并一下,当然也是好玩的事,乐得我们“坐在云端看厮杀”。只是有些不堪的是,杨先生的弟子王贻樑老师,就坐在第一排听讲。
68 学林闻见录/刘永翔
客有于朱公东润座上盛赞无锡国专之美者,以为先生受知唐公蔚芝,且尝任教于该校,必服膺其办学宗旨也,曰:“安得国专复校乎!”先生正色曰:“复他作甚!”
77 “几番风雨”与“一片江山”——梁启超一副集宋词联的流传史/胡文辉
“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本就是辛弃疾、姜夔的名句,而一经梁氏拈出,对仗工丽而意境遥深,于辛、姜词更添异彩,甚至可以说,在原词之外另外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意义世界。
95 掌故家的罗生门/励 俊
从最初主动邀请朱朴合资购买,到后来被追问时改口反劝朱朴放弃,吴湖帆的前后态度大相径庭。这实在是耐人寻味。至于他忽然忿忿地“大怨誉老之误了我们的好梦”,更像是在朱朴面前演了一出戏。
113 从廉庄到蒋庄——再谈西湖小万柳堂始末/艾俊川
面对当日“足以自豪”、如今改换门庭的小万柳堂,廉泉表现出一派非主非客、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蒋国榜邀请他“得闲来往”,他迟迟没有行动。这个约会始终停留在邀请状态,廉泉自西湖小万柳堂脱手,再未回顾。
129 叶恭绰逼债记/郑 重
张葱玉曾一度经济拮据向叶恭绰借款,因无钱相还,遂以书画作价向叶恭绰还债。收藏者多注意书画的流传有绪,但背后故事很少有人注意研究。深究下去,书画流传,特别是在同代之间的流传多和债务有关。叶恭绰、张葱玉这段书画流传转让的因缘,不仅有趣,而且于书画流传的历史和方式而言,都是极有价值的事例。
141 故宫人物片影/聂崇正
壮劳力不能大材小用干这样的活儿,于是唐兰和罗福颐两位先生担当起了此项重任,为此给他们二位用芦苇搭了一处小小的棚子,以遮风挡雨。两位矮矮胖胖又戴了圆圆眼镜的老者,就在棚子里轮流值守,这处芦苇棚子被戏称为“熊猫馆”。
150 市道交/范旭仑
美言可以市。刘孝标《广绝交论》于“势交”、“贿交”、“穷交”、“量交”四流外,更立“谈交”。因为赞美是无形中的贿赂,没有白受的道理。
155 傅增湘逝世的日期/宋希於
傅增湘故去之时,陈毅根本不在北京。而他在北京时如果亲自上门探望,就一定能见到弥留中的傅增湘,那种周恩来派陈毅持函探望,未及相见而傅增湘已病逝的说法,更是虚妄之至了。
165 题签之疑引出的故事——沈燮元《屠绅年谱》出版始末/高克勤
友人安迪觉得《屠绅年谱》的题签不像沈先生说的是吴湖帆写的瘦金体,而像沈尹默写的,遂撰文质疑,并让我找一下档案求证。通过档案发现,在《屠绅年谱》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有那么多现在被公认的名家参与其中……
180 海山仙馆及《海山仙馆图》/许礼平
潘飞声的这种感念畴昔,该比旁人都深切。荔枝涌上园林群以潘、叶两家为主,这在前面说过。潘飞声既是潘德畬的侄孙,又是叶梦龙的曾侄外孙,那么他的感慨该是双重的。
209 吴湖帆和周鍊霞的三场约会/刘 聪
同伤于中年哀乐,互许为人生知己,这才是吴、周二人能走到一起的关键。周鍊霞也正因为人生中遇到了一份难得的理解与慰藉,才渐渐敞开心扉,接受了这段本来不易成就的感情。
221 外祖父涤庵公摭忆/沈厚鋆
一次我去湜华先生书斋“音谷”拜访,先生以一副对联见示,下款署“癸亥八月李诜”,下钤白文“李诜”印、朱文“思本”印。湜华先生说这是他父亲王伯祥于上世纪50年代逛琉璃厂所得,但一直未能考证出作者为何方人士。我说,这是我外祖父的手笔。
245 记“文革”后召开的古代度量衡学术会议/丘光明
我把当年初拟选入度量衡这个课题的过程写下来,留给对度量衡史有兴趣的年轻朋友了解一些掌故,更是留下对那些德高望重的先生们的敬仰和纪念。
263 少为人知的“中国画创作组”/胡桂林
“中国画创作组”,顾名思义,就是邀请全国知名画家完成国家交办的中国画创作任务的专门机构,是现在中国国家画院的前身。
272 艺兰逸闻录(下)/梅 松
白蕉兼工写兰,与传统的墨兰画法大不相同。据其自云:“父亲业馀种花,有几盆兰花是名种,我经常帮助他在清明前后翻种和管理。由于晚上看到壁上的兰花影子,我每天写字后写兰,注意兰品种和成长……”
286 编后语/严晓星